第七章 秘密战线
一
滇南抗战,中国共产党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云南很多地下党员参与了抗日宣传和社会调查,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朱家璧
当时,虽然实现了“国共合作”,但是,在一些地方,我党的活动仍处于秘密状态,有的地方党组织甚至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
据载,1937年9月中旬,中共滇黔桂边区委员会派往香港参加中共南方临时委员会举办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策略训练班学习的朱国英,带领上级党组织派来的张凡(注:即张光夏)等4人,从香港回到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司令部驻地富宁县者兰村,向根据地负责人滕静夫、黄德胜、赵润兰等人传达了“西安事变”后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今后的任务是实行国共合作抗日,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边区党委还在者兰村召开抗日誓师大会,革命游击队、赤卫队和附近群众到会2000人。10月至12月中旬,中共桂西区特委就合作抗日问题与国民党百色当局在百色进行谈判,决定将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和右江下游赤色游击队第2联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5路第1预备军第8、9独立团开赴前方抗日。随后,黄德胜、李家祺、朱国英率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主力400余人到广西田州集中,韦高振率200余人到百色集中待命。滕静夫、岑日新、谭统南、傅少华等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负责人留在根据地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1938年1月,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在田州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独立团,团长韦高振。田州改编后第8独立团离开田州北上,后编入国民革命军第7军171师。朱国英等23名干部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到延安抗大学习。赵润兰、李家祺则返回右江继续宣传抗日活动。7月,中共云南省临时工委派云南大学地下党员龙文池来到西畴兴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学校教书过程中创办《新力周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唤醒民众,团结抗日。是年,中共云南省工委又派地下党员颜绍文、彭子光来到麻栗坡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颜绍文在麻栗坡简易师范学校发动师生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抗日宣传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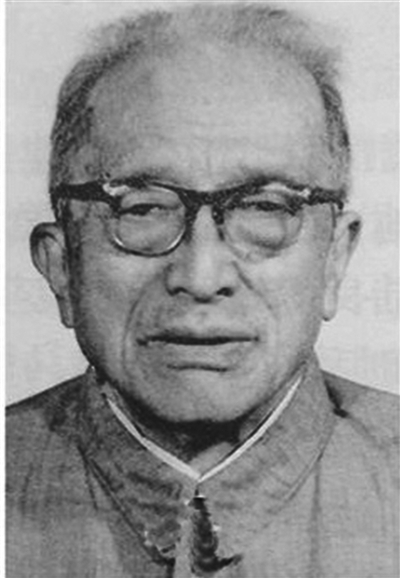
张子斋
1939年8月,云南省工委再次派龙文池和一批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回西畴、麻栗坡地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畴阳中学组织师生开展抗日宣传,出墙报、画抗日宣传画、组织歌咏队、教唱抗日歌曲等,逢街天上街宣传,并在学校增设了抗战知识课程。同原在蚌谷小学任教的程先培(民先成员)取得了联系,共同开展社会调查,宣传抗日救亡。之后,云南省工委先后派出党员邓永寿、包松泉到麻栗坡简易师范学校任教,以教书的形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宣传。
1940年7月,中共云南省工委派西畴籍党员张声仁到畴阳中学,以教师身份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在学生中教唱抗日歌曲,讲解抗战知识,组织宣传队出墙报、写标语等,进行街头宣传。抗日歌曲在兴街地区迅速流传开来,抗日民主气氛异常高涨。9月,云南省工委第三次派龙文池到西畴、麻栗坡等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召集程先培、颜绍文等在程家坡开会研究活动计划,决定在西畴、麻栗坡组织抗日宣传队。西畴由程先培负责,麻栗坡由颜绍文负责,开展抗日宣传和社会调查。
1941年5月,中共党员梁惠被蒙自地下党委派到麻栗坡工作,与邓永寿取得联系后安排在田蓬任教,以教书的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月,在麻栗坡、西畴活动的中共党员在西畴老街畴阳中学成立了中共西(畴)麻(栗坡)党支部,书记黄禹臣,委员刘清林、张声仁,有党员6人,直接受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负责领导西畴、麻栗坡地区的工作。中共西(畴)麻(栗坡)党支部成立后,仍以学校为阵地,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组织学生学习进步书刊、出墙报、唱抗日歌曲等,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不久,西麻党支部的党员先后被捕,党支部被当地国民党驻军和地方政府破坏。
1942年2月,西麻党支部遭破坏后,许多党员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在田蓬任教的共产党员梁惠继续积极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籍,团结了一批进步学生,并于同年4月组织成立“励进社”,引导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43年7月,梁惠将“励进社”改为“滇黔桂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发展到40余人。
二
中共文山州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文山的抗日战争》一书中,记载了中共地下组织积极参与滇南抗战、宣传抗日救亡活动的一些情况。如,中共地下党员邓永寿1983年5月26日在《奉命还乡——西麻地下党的活动情况》一文中提到:
1940年10月,本人奉中共云南地下党领导马子青同志之命,从昆明回到麻栗坡开展工作。
在回乡途中,我带着党组织的介绍信,到畴阳中学(今西畴二中)与张声仁同志取得了联系。到家(麻栗坡)之后,即受聘为麻栗坡简易师范学校教员,以教员身份作为护,开展地下革命活动。
12月,包松泉也带着组织介绍信来到麻栗坡,经我介绍,他也被聘为简师教员,共同开展工作。

这段时间,我仍保持与省工委负责同志马子青的联系。按照组织的安排,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坚持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争取抗日救亡的彻底胜利而斗争。在学校里,我们通过教学来宣传抗日救亡活动,启发学生的进步思想,组织“读书会”,课外给进步青年学生介绍一些进步书刊,组织学生出墙报,教唱抗战歌曲,深受欢迎,影响很大。寒假中,我与教师常矩有曾应督办梁誉的邀请参与边游,借此机会,到各地区写标语、画漫画,宣传抗日,并为将来一旦开展游击活动作了地理和民情的考察研究。
1941年5月,麻栗坡督办署和学校为了向兴街驻军198师师长郑挺锋祝寿,责成学生前往演剧、唱歌,以资助兴。学校叫我与包松泉负责作表演指导,我俩经过研究,他负责指导毕业班演出歌剧《八百壮士》,我负责指导第二班学生演出《太行山上》。两出剧都是宣传抗日剧目,所唱歌曲也是当时全国流行的抗日名曲。在简师公开预演时,就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到兴街演出后更是受到赞誉,再度被邀请到老街演出,影响所及,麻栗坡街头巷尾的大人小孩几乎都能唱出两出剧的全部歌曲,一些小孩还在家门口、马路旁模仿演出《太行山上》。
借到兴街演出之机,我与包松泉到畴阳中学会见了张声仁以及后来的两名党员黄禹臣和刘清林,经研究,我们秘密组织了西(畴)麻(栗坡)党支部,黄禹臣为书记,张和刘分别为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党支部成立后,曾在兴街公园和老街开过两次支部会,碰碰头,交换意见,讨论今后工作任务和联系方法等事宜。不久,党员梁惠又带来了组织介绍信和我联系。因麻栗坡简师教员已满,我设法为他安排工作,通过教师常矩有的关系,介绍他到田蓬任教,并与西麻党支部接上组织关系,他独自在田蓬地区开展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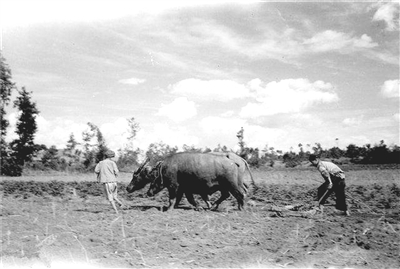
抗战大后方的农民在耕种
我们疏散到麻栗坡不久,国民党便加强边防的力量,驻文山的关麟征部队,便后派了两个师的兵力,部署在兴街、麻栗坡一带,另有1个宪兵营,他们的特工人员经常出入学校,还有县党部的人员在学校兼职。我们的活动明显地受到监视和干扰,情报被撕毁,抗日活动被停止,我曾被警告。畴阳中学的情况比我们更为严重,据张声仁告诉我,当地驻军头目和便衣特务进驻学校,出出入入,对他们的监视很严,简直难以公开活动。6月份的一天,我到老街(畴阳中学驻地)找党组织汇报情况,因不可能过多耽误时间,以免引起他人注意,最后决定由张声仁跟我一道以去马朵姐姐家玩为掩护,一路上边走边谈,详细分析了目前形势,认为工作已无法开展,应该设法撤退转移。后经支部决定,让我和包松泉先离开麻栗坡返回昆明,他们几个分批撤退。按党支部决定,7月份,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机会,我与包松泉借口到西畴我父亲处度假,便离开了学校。当天下午,路经畴阳中学时找到张声仁,请其告诉党组织,我们上昆明去了。张说:“你俩先走,我们随后就来”,就此告别了。8月,我们到昆明不久,就听到同乡人说,文山、老街的一些教师,已被视为嫌疑分子被当地驻军逮捕了。9月中秋节后,我亦在昆明被捕,关押在云南省党部。一个月后,被组织营救出来。但是,中共西麻党支部惨遭破坏。我在狱中的表现,已有肯定的结论。
三
据史料记载,1941年5月,时任滇军第1旅第2团第3营营长的中共地下党员朱家璧到滇南前线蒙自芷村的防地就职。朱家璧回云南,是有其原因的。1941年1月,在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反共行动甚嚣尘上之际,朱家璧肩负着周恩来、陈云等领导的重托,离开重庆返回云南,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审慎地在滇军中开展统战工作。
朱家璧,云南省龙陵县人,早年参加滇军,1938年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陕北公学教育干事。1940年被秘密派回云南,在滇军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先后任营长、副团长、团长等职,并以此为掩护,把许多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隐藏在滇军中,广泛接触滇军中上层军官,多渠道开展党的统战工作,积极准备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46年,朱家璧按党组织的安排离开了滇军,疏散在外,任党的特委书记。1947年,朱家璧回到云南,之后,组织领导了滇东南路南圭山、弥勒西山起义,组建了云南人民游击武装主力部队——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1纵队,任司令员,参与并指挥了奔袭师宗、围攻丘北、攻克广南、南下桂西、河阳整训、转战开广等一系列战斗和军事行动。
据《朱家璧在滇军的统战工作》一文载:
1938年,二十几岁的朱家璧化名“陶隐潜”,主动脱离滇军,奔赴延安。如今,怎样按周恩来、陈云的指示再打回滇军去?他决定从他在滇军中的老关系入手。
朱家璧先找到时任第22师师长的黄埔军校第八期老同学、卢汉的婿弟龙泽汇,同他讲了自己离开滇军后,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的情况,并告诉他,自己“这次是请假回来探亲的,还准备回去”,看龙泽汇如何反应。龙泽汇听后说:“你不要再出去了,哪天我们两个去看望第一旅旅长卢浚泉。”卢浚泉1924年入黄埔军校轮训班学习,结业后留校任第三期学生队区队长,1937年任滇黔绥靖公署近卫第一旅少将旅长。卢浚泉是第一集团军司令官卢汉的幺叔,朱家璧原在滇军时就与他很熟悉。第一旅是龙云很器重的主力,抓住卢浚泉,对做好滇军统战工作十分重要。
见到卢浚泉后,朱家璧告诉他自己是请假回来探亲的,并有意向他透露了一些延安的情况,如八路军的治军方法、部队的精神面貌等。卢浚泉听后说:“全民抗战,云南也需要人,你不要再回去了,就留在我旅,到二团三营去当营长吧!”就这样,朱家璧顺利地打入了滇军。
1941年6月中旬,朱家璧到了三营驻防的蒙自芷村,去看望在滇军工作时的老同僚和老部下,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一次,卢浚泉要朱家璧给全旅官兵作报告,他着重讲了战争的性质问题,指出罪恶的轴心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反人类的,是必败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的,是必胜的;还宣讲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和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事后,有些军官表示,朱家璧的报告内容很新鲜,听完感觉开阔了眼界,也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可以取得最后胜利的。
朱家璧了解到滇军中存在军官打骂士兵、枪毙逃兵等恶习,官兵关系很紧张。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士兵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就不能有效提高战斗力。于是,他召开全营军官大会,规定全体军官不许再打人骂人,不准枪毙逃兵,同时宣布经济要公开,还撤换了两个生活腐化的连长,得到大多数官兵的拥护。

第一集团军士兵在训练
1941年11月,第一集团军司令卢汉组织营以上军官二百余人到驻防文山的第九集团军关麟征部参观演习和营区建设。参观结束后,卢汉留下朱家璧等人开会,听取他们对今后部队建设的意见和建议。朱家璧结合自己在延安的亲身经历,提了三点建议:一是盖简便营房,不住民房,这样既有利于军队的训练管理,又有利于搞好军民关系;二是积极开展文体活动,使军队活跃起来,增强官兵体质;三是自己动手,养猪种菜,用以改善士兵生活。这些建议得到了卢汉的肯定。1942年春节过后,朱家璧便率领三营动手,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斗,盖成了全集团军第一所营房。
事实证明,只要按照八路军的办法带领部队,即使是旧军队,也能改变面貌。有的士兵编快板称赞道:“三营好,吃得饱,学军事,学文化,不打骂,不想家,打日寇,保国家。”
为宣传抗战,朱家璧趁卢浚泉到该营视察的机会,向他建议:“现在,许多连排军官的知识都很贫乏,有些人连报纸都看不懂,请个顾问来讲世界知识、时事,进行政治常识及形势教育很有必要。”这一建议得到卢浚泉的批准。此时,曾在第三国际工作过的专家刘思慕正好从印度尼西亚回到昆明,朱家璧便亲自请他去当政治顾问,并安排他一家四口住进自己的营部。刘思慕对朱家璧交给他的这一工作十分负责,给官兵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史、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及德、意、日法西斯为何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问题;还在全旅连以上军官训练时讲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等。在三营的日常训练中,朱家璧也经常给全营官兵讲《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政治常识》等。
1943年初,滇军第一旅改编为暂编第十八师。3月,朱家璧升任第三团副团长。他上任后,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写了一个讲课提纲,给全团军官讲课。有人说朱家璧在搞“赤化教育”,要“赤化滇军”,但因为朱家璧在滇军中人缘很好,也没有人能把他怎么样。
1943年9月,为进一步开展工作,朱家璧在大庄村成立了40多人的“艺术工作队”,兼任队长,后请来进步艺术家王旦东为副队长兼编导。队员多为在昆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进步学生、青年,如后来成为云南民歌歌唱家的黄虹等,打造了一支特殊环境下的抗日文艺宣传队伍。
朱家璧还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请专家(如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赵讽等人)到艺工队讲课、办训练班。1942年,郭沫若在考证明代文学家杨慎《滇载记》的基础上,在重庆创作四幕话剧《孔雀胆》,该剧先在重庆首演后,又到各地巡演。1944年8月,剧团到昆明巡演时,朱家璧带艺工队去观摩学习。他还曾带队员到李公朴家听形势报告。这些学习让大家懂得了应该爱什么、恨什么。
朱家璧组织艺工队先后排演了老舍、宋之的写的反映回汉民族团结抗日的四幕话剧《国家至上》、舒非的独幕剧《民族公敌》以及在解放区、根据地流行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兄妹开荒》等数十个剧目,还排练了一些有影响的救亡歌曲,如《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在太行山上》《胜利进行曲》《炸桥》《丈夫去当兵》等等。朱家璧还将《八路军进行曲》后两句“向华北的原野,向塞外的山岗”改为“向西南的原野,向滇越的山岗”,并改歌名为《军队进行曲》。他经常带队到连队慰问演出,教官兵唱进步歌曲,从而改变了部队的精神面貌,得到了卢浚泉的赞赏。
当时,华宁县盘溪镇驻有九十三军的特务营和战防炮营,十八师的炮兵营、辎重营和工兵营。卢浚泉决定成立一个督训处,想找一个得力军官去统管这五个营。他首先就想到了朱家璧。5月,朱家璧就任九十三军督训处主任。
卢浚泉到盘溪视察,朱家璧利用这个机会,同他谈了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龙云的关系,对他说:“蒋介石这个人心毒手狠,是从排斥异己、吞并异己,到消灭异己起家的。为了建立他的独裁统治,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现在,他在云南摆了四个集团军,这个情况,很值得注意。如果蒋介石动起手来,云南怎么办?”卢浚泉沉思后说:“是啊!很值得注意。”
1945年初,蒋介石将滇军主力六十军、九十三军以及中央军五十二军、广东的六十二军组成第一方面军,卢汉任总司令。卢汉便调朱家璧到担负警卫任务的特务团任团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8月1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达“第一号总命令”,对同盟国各自的受降区域作了划分:除满洲外,中国境内的所有日本部队以及台湾和北纬十六度线以北法属印度支那的全部日军,由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受降。蒋利用这一命令,实施调虎离山之计,任命卢汉为第一受降区受降主官,调卢汉的第一方面军开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9月,又令暂编十九师龙云之子龙纯武部和暂编二十三师潘朔端部入越,致使龙云多年训练、装备起来的留在云南的部队仅剩下其次子龙绳祖率领的二十四师以及宪兵团和警卫营。
朱家璧看出了其中的玄机,找到已升任九十三军军长的卢浚泉,对他说:“驻云南的中央军有四个集团军,为什么不调他们去越南受降?而偏偏要调滇军去呢?你要给卢汉和龙云讲讲,如果把滇军都调往越南,蒋介石对云南下毒手时,拿什么力量来对付?后果不堪设想。”果然,后来的局势发展不幸被朱家璧言中。
四
关于滇南抗战,朱家璧回忆道:“在短时间内,由于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与民主,带来了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初步团结,工作与训练的劲头比以前大多了,军风纪律比以前好多了。”1941年,中共中央派朱家璧回云南,到达重庆时,周恩来曾指示他要“以进步的面貌出现”,在实际的工作中,他把八路军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运用到他所带领的部队中,并以明显的成果去影响滇军。
好榜样的影响是巨大的,“时刻准备着”痛击来犯之敌的滇南抗日部队呈现出“新军人新军队”的喜人景象,这与朱家璧的“传经送宝”有着直接关系。他后来在回顾这段经历时写道:“山上山下,又拉又唱,一片欢腾。各连还开展了劳动竞赛,你追我赶,进度很快。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斗,便盖成了全营的宿舍、伙房、图书室、文化室、厕所和岗亭。部队搬进营房后,我们还修了个大操场,写了标语,画了宣传画,栽花、种树、种菜,既美化了环境,又搞了副业生产。”
1941年秋,朱家璧曾到石屏师范学校作过《民运工作漫谈》的专题演讲,向师生宣传团结抗日,反对消极抗战、反对卖国投降的道理,加深了师生对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卖国投降的仇恨及增强了热爱中国共产党的信心。
1941年冬,李公朴到石屏,在城区、宝秀住了1个多月,作过多次演讲,和学生座谈,介绍晋察冀边区军民的抗日活动,对鼓舞人民抗日情绪以及引导革命青年向往延安、奔赴延安,起到了良好的教育作用。
据史料记载,1943年,周恩来在重庆与龙云会面,给龙云作了进一步的思想交流工作。这一年的10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华岗、周新民等同志先后到云南帮助民盟建立地方组织,继续做龙云等人的工作,争取他们与共产党合作。在华岗的倡议下,西南联大、云大等一批专家教授,组成“西南文化研究会”,大家在抗日救亡、争取民主和进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从而“掀起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新高潮,准备迎接抗日战争的新胜利。”此后,昆明的民主运动掀起了新高潮,并且使昆明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民主堡垒”。龙云亦于1944年底,秘密加入了民盟。
1943年初,第60军在滇南蒙自新安所作兵员补充和整训,补充团第1营营长杨滨是1935年由第60军地下党员费炳介绍入党的。由于杨滨有“云南陆军讲武堂军士队”的学历,军事素质过硬,1944年被调往新组建的第60军直属的骑兵搜索营任营长,这是60军提高部队攻击能力的努力之一。同年底,经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张子斋介绍,近10位“西南联大”学生进入该营工作,这些学生兵大多被培养成技术骨干,有的还加入了党组织。1941年,张冲被任命为第一集团军第2路军总指挥时,特意安排了中共地下党员张子斋为秘书,张士明为特务营营长等,以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和战斗力。
凡此种种,“国共合作”就是以这样一些特殊方式,为滇南作战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的提高贡献力量,使部队保持和发扬了滇军“攻必克、守必固”的光荣传统。包括张冲指挥的第2路军在内的滇南作战部队,在滇南一带发动各民族群众,群策群力,支持抗战;滇军第60军第184师内部的地下党组织,也积极行动起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国民党军中及滇南党的地下组织的联络、协调、帮助下,文山、红河地区驻军联合沿边(注:指中越边境)少数民族土司武装一道合作抗日,仅进入编制的就有8支游击队,其支队司令除1人是头人外,其他均系土司担任,形成了军民一心、万众一心、鱼水情般的军民合作共同抗日态势。
日军占领越南后,建水师范学校校长刘宝煊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1940年春,该校特师班毕业,刘宝煊在毕业生中秘密组织了抗日救亡团体“丹心社”,并与“丹心社”成员一起商量,一旦日军侵入滇南就上山开展游击战争。学校改为建民中学后,十分需要进行军事教育,并开展军事技能的训练活动。恰好驻军第2路军中的中共党员也需要跟建民中学密切合作,通过对学生的军事训练更好地实施抗日游击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
1940年秋,滇军第一方面军第2路军指挥部内的秘密党组织从严峻的抗战形势出发,作出一旦日军入侵滇南,立即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决定和行动部署。毕业于延安抗大、后被党组织派回云南的共产党员何现龙与第2路军总指挥张冲有良好的亲戚关系,其随张冲到建水,与特务营营长张士明等共产党员作了商谈。何现龙认为,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一方面要有适宜的地理环境,另一方面要有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此,他深入到红河两岸的蒙自、屏边、金平等地考察地形、交通、河流、桥梁等情况和社会状况,之后再次进入南盘江两岸的弥勒、泸西、路南、陆良、师宗、丘北等地广大山区作更深入的考察和调查。何现龙觉得,这些地区山势险峻,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群众基础好,回旋余地大,有利于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于是,何现龙在泸西县云兴乡新庄科邀约在当地有影响的彝族青年、积极分子窦崇孝、杨福安、杨文光、金发友、张克忠、黄恩培等人集会,向他们宣传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商议在少数民族地区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武装斗争的问题,得到了窦崇孝等人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1941年8月以后,经第2路军总指挥张冲同意,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张子斋、徐日宗、方正、宁坚、张士明等先后到建民中学任教,宣讲党的主张、革命道理和教军事理论。指挥部特务营的周连长每天由白家营带上10多名班排长到学校开展军训活动,给学生进行真枪实弹的操练。为了提高学生的军事素质,学校组织学生和第22师邱开基部的官兵一起进行实弹军事演习。这一时期,上午坚持上文化课,下午主要进行军训和政治学习。刘宝煊、方仲伯为了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军事训练,在学生中成立了军事组、宣传组、民运组、救护组,并对口开展了大量的训练活动。当时,学校的气氛紧张、热烈,学校门口有学生持枪站岗,同学们随时准备着奔赴抗日战争的前线。
抗战期间,坚持在滇桂边、中越边境地区的共产党员,不畏恶劣的斗争环境和形势,坚持从事党的工作。原边区党委书记、革命游击队政委滕静夫和革命游击队大队长谭统南、岑日新,赤卫队队长罗子德等仍在边境沿线从事党的抗日救亡活动。谭统南等组织的抗日游击大队不断发展壮大,队伍达到近400人。他们英勇抗敌、不怕牺牲、血洒疆场。
(未完待续 本文未经作者授权不得转载)
(记者 林浪平)
(来源:文山日报·文化)
(编辑:曾炜炜 排版:张振飞 审核:侯佑琴)






















